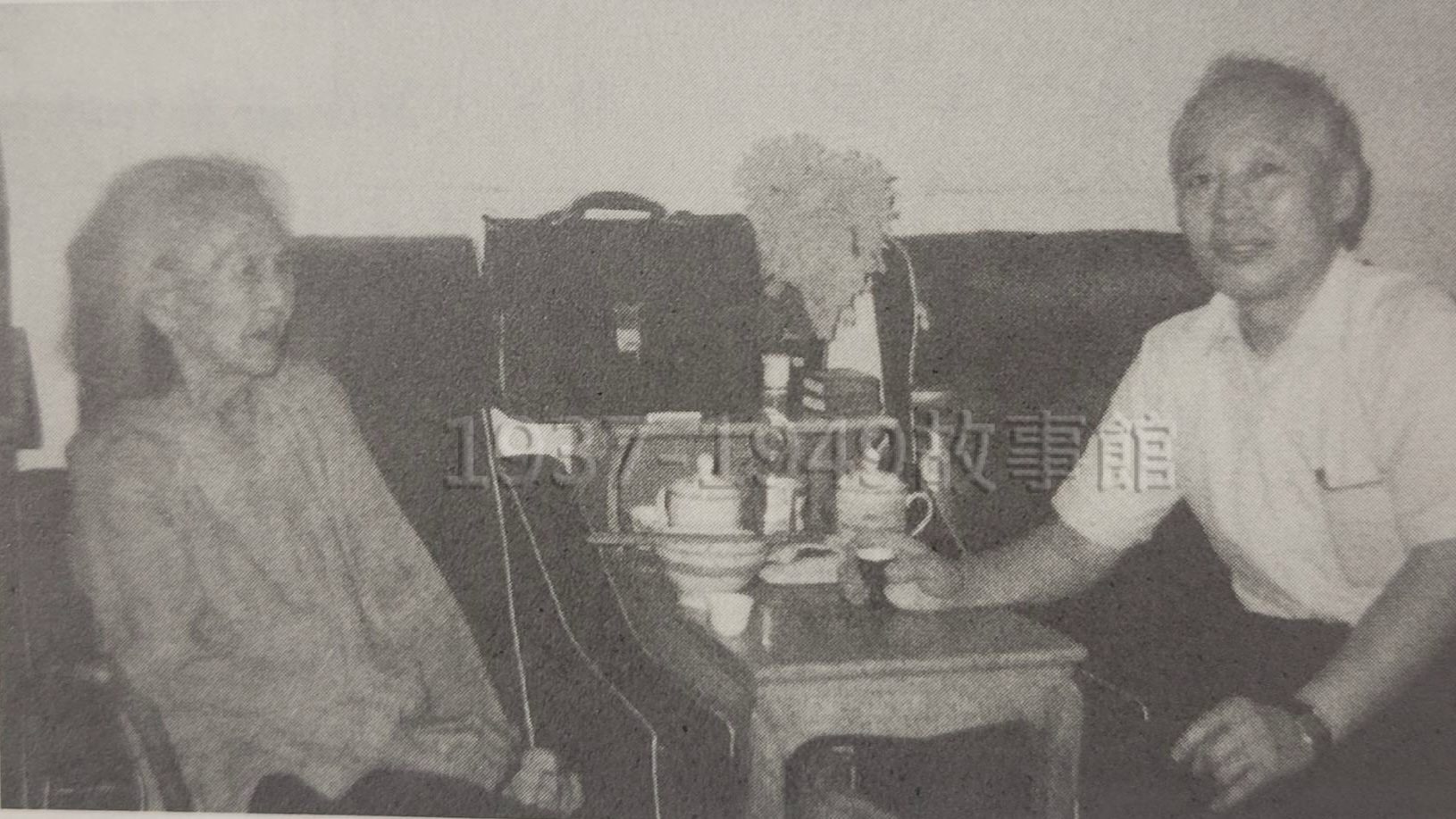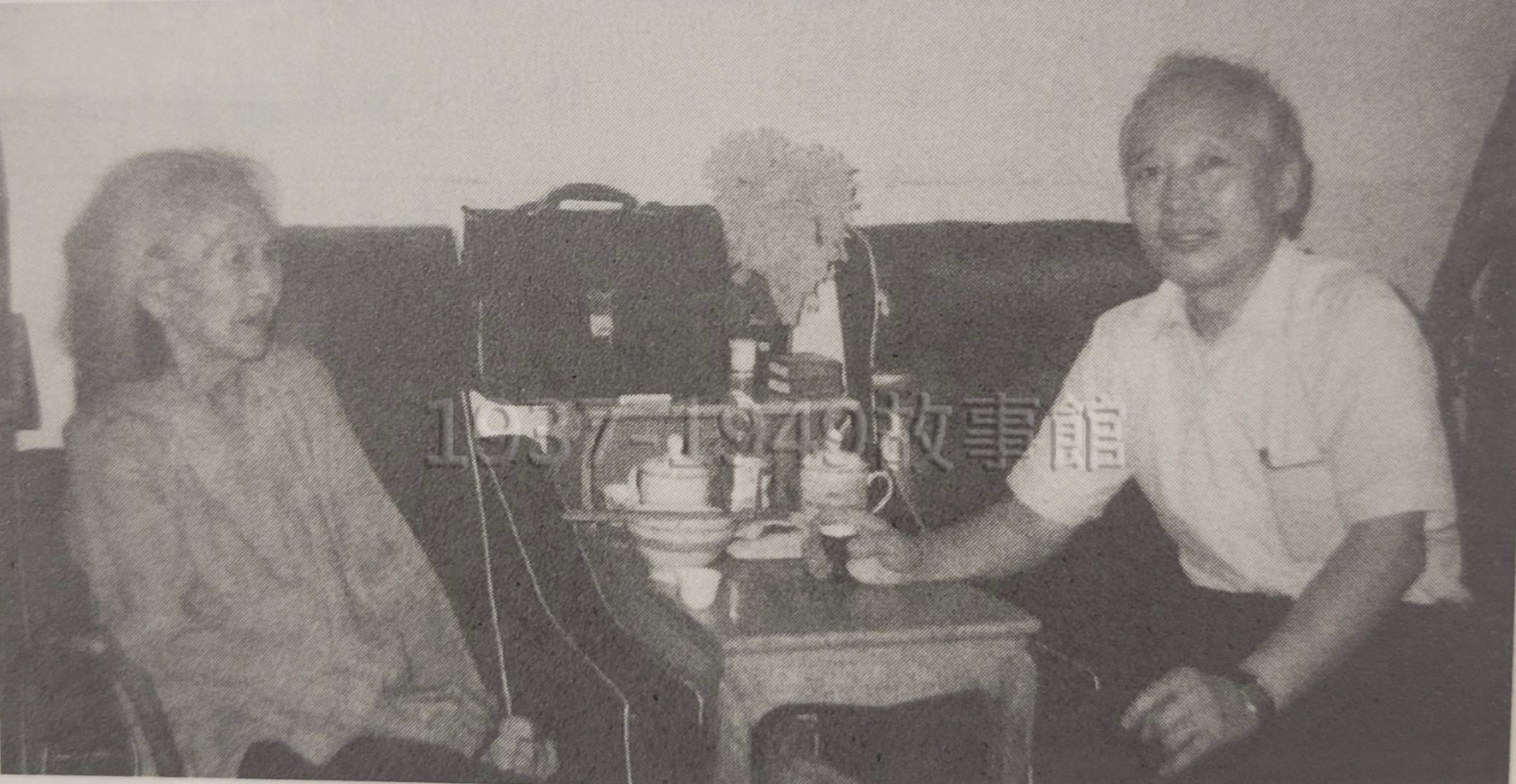
圖/葉楷翎攝
我的老家在山東嶧縣澗頭集,距離徐州約一百里。祖父原是佃農,但到了我父親,可以說是一位小地主了。因為他一面種田,一面製做麻油賣錢,每賺點錢就買點地,勤勤懇懇終於有了一百畝地。
我1936年出生時,日本勢力已經由東北向華北延伸。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,日本全面侵略中國。國共雖然號稱合作抗日,事實上正面戰場都是國軍在對抗日軍,共產黨在敵後打游擊。
1938年台兒莊戰役後,日本人進入山東,但是還無法有效統治鄉村地區。對國民黨來說,山東變成敵後,不管了,但共產黨也還未成氣候。在澗頭集,國民黨游擊隊、共產黨游擊隊和日軍輪流來抓伕要糧,加上土匪小偷橫行,地方上治安很糟。
日本佔據山東後,是透過「華北政務委員會」來管理山東地區政務的。這是一個類似汪精衛在南京組織的國民政府的機構。委員會設了省長、縣長、區長,還有警察維持治安。我家鄉屬嶧縣第八區,區長是龍希貞。他是嶧縣澗頭集人,父親打游擊,一開始屬八路軍,被國民黨打敗後變成國軍。國軍跑了,他又加入日本陣營,那個時代多半就是這種情形。龍希貞有個外號叫「龍瓜屋子」。瓜屋子是指北方種瓜田地裡蓋的小房子,用來防止小偷偷竊作物。據說龍希貞在瓜屋子和女人野合,所以有了這個外號。
家鄉原本只有私塾,1942年,華北政務委員會在嶧縣第八區辦了小學,家鄉終於有了學校。抗戰勝利後,國民黨來嶧縣接著辦,我因此才有機會讀小學、考中學;共產黨來的時候也才會跟著縣立中學南遷。
在偽政府時期,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就需要上日文課,但在我小學四年級時日本投降了,因此我錯過了學日文的機會。其實當時我還挺希望學日文的;之後想要學就比較難了。
共產黨標榜打敵後戰,實際上他們不跟日本軍隊直接衝突;直到日本快投降時,才專打日本成立的維持會[2],也就是日本扶植的偽政權。維持會徵糧、徵伕,也維持治安。共產黨會趁夜間視線不良的時候翻城牆進來,攻擊維持會。當時日軍駐守在我們東邊約30華里的台兒莊。他們得到游擊隊進攻的消息,會派一個大約二、三十人的小隊來救龍希貞。那時候日軍的槍比較好,開槍時會響兩聲,但中國自己造的槍,開槍只響一聲。所以日軍一開槍,共產黨就知道維持會的援軍來了,趕緊撤退。
抗戰快勝利時,龍希貞判斷澗頭集是一個比較小的鎮,會撐不住,接著台兒莊也撐不下去,於是他退到嶧縣城,但最後嶧縣城也被共軍攻下,龍希貞被俘。不久,他被押解回澗頭集。龍希貞掌權時,為維護地方秩序,派兵到鄉下打共產黨,殺了很多共黨游擊隊員,執行所謂「清鄉」政策。清鄉期間,龍希貞將被俘共產黨頭子的頭砍下,掛在澗頭集街上的槐樹下,我們小孩晚上都不敢出來。龍希貞被俘後,共產黨就在他自己軍營的大門口前,把他槍斃了。
大概到1943年後,山東地區的國民黨游擊隊已被共軍消滅殆盡,因此1945年抗戰勝利,國軍在大後方,要過來很不容易。率先進入我們家鄉的是共產黨,而他們的政策是清算地主,說地主壓榨佃農。我們家被數落罪狀後,田地都被分給了佃農。
這些記憶我印象滿深的,雖然那時我是小孩,也會從大人那邊聽來一些消息。人們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評價很難說,基本上,還是要看評論的人是無產階級還是地主。無產階級當然喜歡共產黨,因為他們可以給土地;但我們是地主。以我自己的經驗,日本透過維持會統治山東的時期,家鄉的生活是最好的。龍希貞曾說:「平常我不在澗頭集徵稅、徵伕,萬一哪一天,共產黨包圍了澗頭集,我無法去四鄉徵稅、徵伕的話,你們再幫我。」因為沒有稅賦與勞役,我們都覺得這個政權很好。而且有日本人維持秩序,很安定。
共產黨認為地主一定有錢;他們不但鬥爭父親,還向我們家要兩百銀圓。家中財產所剩無幾,唯一的錢是抗戰前政府發行的法幣。當時一般人的觀念覺得紙鈔比較好保管,家人把剩下的法幣裝在瓦罐裡,埋進地下。結果抗戰結束挖出來,又因為貨幣貶值,這些法幣變成廢紙。
父親拿不出錢,被共產黨關起來。當時家中有奶奶、母親、一個妹妹、我和兩個哥哥;姊姊已經出嫁。一天夜裡,父親越獄逃出來。因為外婆家在國軍管轄的前馬家,於是父親帶著家中三個男孩子逃了過去。
外婆家裡忽然多了四口要吃飯,無法應付,所以大家都得出去賺錢。當時我才十幾歲,能做的事情不多,就賣起了香菸。以前有一種香菸叫做「紅包」,用紅紙包著,一包五十根。我拆開包裝,把一根根煙放在一個籮筐裡,到前馬家附近的市集賣。一天差不多能賣兩包,賺一點錢貼補生活。
大陸有很多市集,平時除了小舖子,沒有商業活動。市集並不是每天都有,人們約定時間,每十天中有四天會有市集。只有碰到市集時,各個村莊的人才會集中到一個鎮。農人會把自己生產的農產品、手工品和加工品等帶來賣,人才會比較多。距離外婆家比較近的有南北各一個市集,兩個市集離家都要差不多十華里[3],得要走去。
沒有市集的日子,我就在外婆家幫忙放牛。通常一個比較有錢的家庭會有一頭牛、兩頭驢,牛和驢都可以耕田,驢還能馱東西;婦女要走遠路的時候,也會騎驢。外婆家算是中農,大概有三、四十畝田地。我姊姊有時要回婆家,我就趕著小驢送她去。我們家沒有養馬和騾子,驢子一般來講比較溫順,馬比較難管,騾子脾氣更壞,有時騎上去,牠就一直跳,讓人摔下來。
逃到外婆家後,我們沒辦法唸書了。外婆家的表哥不曾唸過書,他跑去延安加入了共產黨。其實在鄉下地方,大家為生活奮鬥,本來就少有唸書的機會,父親願意讓我們唸書,是很開明的。
父親和三個男孩一起逃到外婆家後,國軍曾一度反攻,我們也回了家。但是後來共產黨又來了,逃亡地主的家人還是會被鬥爭。剛好那時嶧縣縣立中學校的宋東甫校長要帶學生去江南讀書。這位宋校長在抗戰時期就帶過學生到四川讀書,所以許多人聽說他要再次帶學生出走,都想跟。當時二哥小學畢業,順利考上簡師班[4],要跟學校走;我才小學五年級,只好以同等學力去考。考試時,每個考生拿個小圖板[5],考卷放在上面,人坐在草垛子上作答。所幸作文「農家樂」受到老師賞識,順利考入初中一年級。
出發
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,家中已經沒有什麼錢了。在農家,動產就是糧食,父親賣了好幾百斤儲存在倉庫的小麥、高粱等糧食,替我們籌路費。離家時的行李就是被子、一些衣服、飯碗、筷子,用來上課的圖板和小凳子綁在背包底下,以便隨時上課。我們由程莊出發,走了30多里路到賈汪,再乘坐敞車[6]到徐州,住在徐州一所中學。我們白天在操場邊上課,吃飯、休息,夜晚搬進教室睡覺。早晨六點起來,把教室打掃整理好,再搬回操場上課。

兩個星期後,共軍已經向徐州集結,我們設法擠上津浦路火車南下;由於車廂裡已經擠不進人,所以大部分同學都坐在車頂。第二天早上到浦口,乘輪船渡長江,由下關坐火車到鎮江,再乘輪船由鎮江渡長江到對面的瓜洲,住在一間破廟及鄰近的房子裡。四星期後,因為國軍在徐州、蚌埠的戰事失利,我們只得繼續往南走。11月,先是跟學校乘輪船到鎮江,再搭火車到湖南棲鳳渡站下車,步行數里到站北的洞尾,在李家祠堂落腳。
到湖南後,山東各地的流亡學校編為八所聯合中學,嶧縣縣立中學改名為「國立濟南第四聯合中學第二分校」。但是兵荒馬亂,學生必須自己跟好隊伍,否則一旦走失,就回不來了。
開始瞭解「飢餓」
我和二哥離開家的時候,身上帶了一些金圓券,但是到了湖南,這些金圓券已經嚴重貶值。二哥提議將剩下的錢買兩雙膠鞋,替換破了的布鞋。但是穿上新鞋之後,我們就沒有錢了。這時候,有的學長打著流亡學生的名號去募捐,募得的錢卻放進自己口袋。
原本湖南省政府把供給我們的米和煤運送到距離洞尾不遠的鄉鎮,由我們自己去扛回來用。但是四月開始,湖南省政府又把米撥到永興縣。由於路途遙遠搬運困難,全校男生和部分老師只好走一天的路,搬去永興就食,晚上住在一間破舊的學校裡。學校的稀飯非常稀,都可以照出人影。到了五月初,共軍渡過長江,湖南省長程潛叛變,湖南省政府自顧不暇,就不再提供食物。
有至少一兩個月的時間,我和同學三三兩兩,被迫上門乞食。一開始,當地人家中較富足,看我們這些流亡學生沒東西吃,還會供給食物。後來上門的學生越來越多,他們支應不起,很多人家索性關上大門,不再理會我們。我和同學還到田裡挖農人收成後剩下來的地瓜,在山上撿點柴烤來吃。此時學校也因為沒有飯吃,暫時停止授課。我們餓一頓、飽一頓,營養談不到。也許在別人看來,覺得我們蠻可憐的,但可能小孩比較樂天,加上大家都一樣,就只是共同想辦法,沒有覺得自己有多可憐。
老師有錢,不必跟著學生挨餓,但學校因為沒有食物,無法上課。二哥看到臺灣新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在長沙招兵,於是決定投軍,臨別前他告訴我,希望我們當中至少有一人將來可以回到家去奉養父母。但是後來他在湖南衡陽遇上李彌抓兵,被派去雲南打投降共產黨的龍雲和盧漢,結果兵敗被俘,二哥加入共產黨。
注解
[1] 《浮生日錄》,張玉法著,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,2023年。
[2] 政務委員會是高層的,地方上叫做維持會。
[3] 差不多五公里。
[4] 簡易師範班。因當時大陸師資缺乏,經過簡師班訓練一年後,就可教小學。
[5] 木製的方形板子,流亡學生將紙放在上面用鉛筆寫字。
[6] 一種沒有頂的火車,在平常用來運煤。